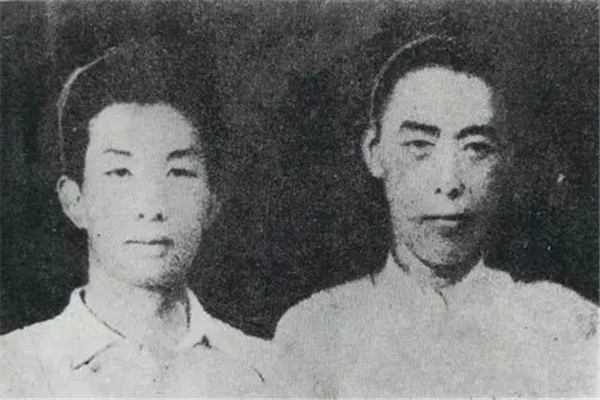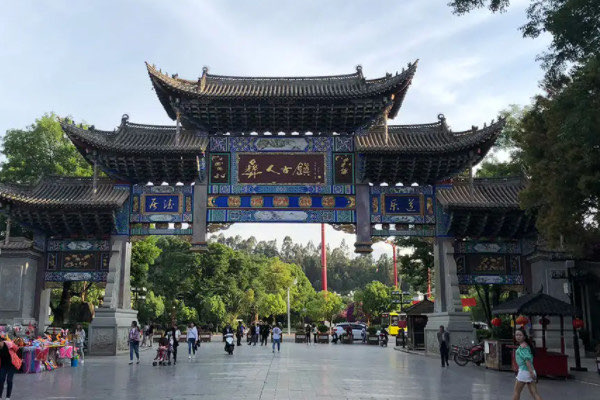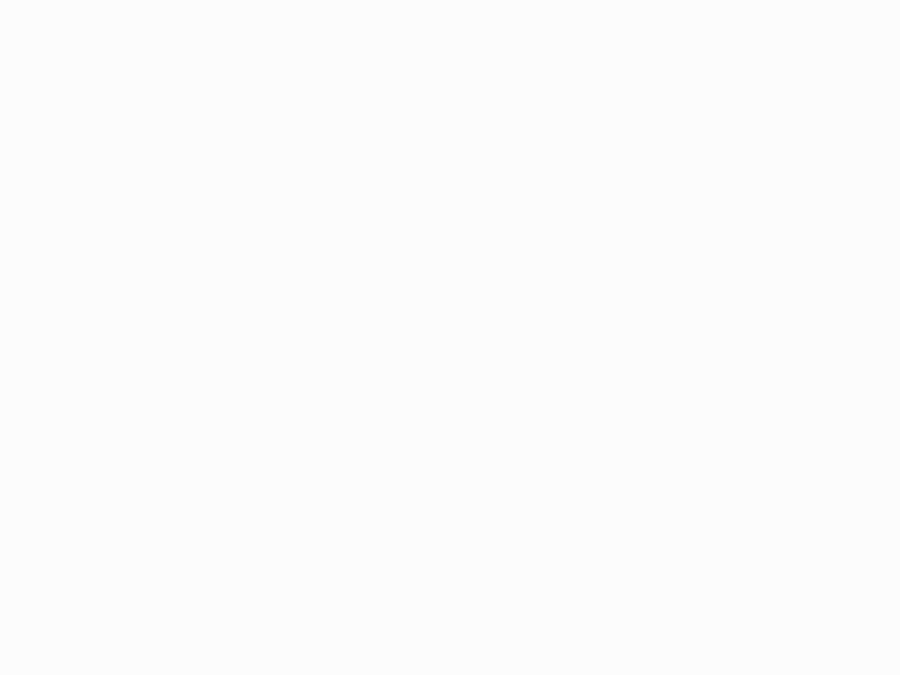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的150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兵分四路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截至8月30日,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部被解除武装,苏联红军在中国和朝鲜人民的有力配合下,一举打垮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多年的关东军和其他日军,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共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日军59.4万人。 作为战利品之一的近60万日军战俘被苏联红军分期分批地押入苏联境内,大部分日本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还有一些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1、日本战俘被安排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为了丰富战俘的生活,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了一些文体活动,当年的日本战俘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回忆道:他曾被关押在莫斯科附近的拉达国际战俘营,“昭和21年(公元1946年)初夏,我们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赛”。在1949年劳改营的新年联欢会上,一出由当年为日本关东军和特务机构效力的中国汉奸上演的京剧《盘丝洞》,竟博得了全场掌声,就连战俘营的苏方管理人员也看得津津有味。
苏联劳改营当局特别重视对战俘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期培养战俘对苏联的好感,同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所指出的:政工教导人员的任务是“确保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不断增长”。为此,除了所长、劳动主任、军医官之外,苏联劳改营当局还在每个战俘劳改所都配备了一名政治部主任,专门负责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工作。【趣探网】
1947年,各战俘劳改营和劳改所先后成立了战俘民主委员会,委员由战俘大会选举产生,其宗旨和任务是对战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其成为一个永远不做反人民事业的初步的民主主义者”,日本战俘丸茂曾担任过战俘民主委员会主任,丸茂原是伪满军校的教官,年富力强,头脑清楚,颇有口才,且会说俄语,因而他被授命专门从事对战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讲授工作,而丸茂所在的战俘民主委员会的其他3名委员则仍必须参加劳动,并不享受丸茂的“脱产”待遇。
劳改所里很快成立了政治学校,每周一、周五晚上7时至9时为政治学习时间,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后来,还成立了一个联共(布)党史研究班,主要学习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1948年以后,苏联劳改营当局又陆续给战俘分发了一些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传》等,都是著作的日译本,政治学习中涌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从1948年开始,其中的优秀者被分期送至地区劳改营本部学习6个星期,再回到原来的劳改所从事宣传和教学活动。
一些战俘通过政治学习初步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础知识,了解了苏联国内的一些现实情况,为了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战俘们还在劳改营里创办了《日文报》,交流彼此的学习感悟和心得体会。此外,他们还在1947年末创办了《新生》板报,用16开的白纸写成文章贴在板上,供大家阅览,板报还登载一些小故事、笑话、谜语等,这些活动无疑调节了战俘们枯燥而繁重的劳役生活。
然而,事实上多数战俘政治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不少讲授者本身就是日本战俘,他们没有系统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因而也就没什么这方面的理论素养,此前更没有讲授过马列主义理论,仅懂得点俄语、有些文化而已,如此就被安排讲授艰涩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现年70多岁的日本东村山市的退休教师益田实,当年是日本战俘之一,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1米73的个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乍一看像是个知识分子,于是战俘民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对我说:‘从明天开始,给大家讲解这个。’这是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厚一公分左右,我只好天天开夜车阅读,然后给人讲解,幸好没有出丑就讲完了,当时可真是如履薄冰啊!”
其次,作为劳改所政治学习活动受众的日本战俘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这也影响了政治学习的效果,不少人都是刚入伍才一两年就沦为战俘了,年纪还不到20岁,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有些干脆就没上过学,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显然比较吃力。
中国末代皇帝、后来成为日本人傀儡的溥仪在押苏联期间也曾参加过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这种政治学习,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感受:“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溥仪尚且听得如此“糊里糊涂”,那些没什么文化的日本战俘听课的效果便可想而知了。
2、苏联劳改营当局盛行做表面文章
日本战俘政治学习效果不理想,还缘于苏联劳改营当局盛行做表面文章,战俘们按照政工人员的要求展示“思想改造成果”,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忠诚和信仰。当局将战俘们的各种活动拍摄下来:“战俘们在食堂就餐”,“战俘们在理发馆理发”,“战俘们在医院就诊”,“战俘们在搞体育比赛”,“战俘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照片还被装订成册,旁边配注了有关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文字或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然后作为“思想改造”的成果送交上级部门。
这些相册不仅是展示给苏联人民看的,更主要是展示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看的,以此表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对人的特别改造功能。至于战俘们究竟真正理解并掌握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多少战俘通过政治学习成为了初步的民主主义者、培养了对苏联的友好情感,劳改营当局则不会太当回事。
而战俘们表面上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也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他们担心一旦流露出对政治学习的不满和厌烦,就会被送到位于苏联腹地的战俘惩戒所,或者会被推迟遣返回国,就连曾经残暴地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摧残反战人士的原日本宪兵也都变得“自觉”起来。
日本久留米市的农夫平野好郎,在回忆苏联劳改营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的有关情况时说:“这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第19号战俘所,时间在昭和22年(公元1947年)2月前后。红军将我们这万名战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原先的宪兵们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击队’,‘民主化突击队’的劳动条件格外艰苦。每天早晚,他们进出营地时,扯着嗓子高唱‘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会给战俘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前文引述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指出:“那些同政工人员有接触的战俘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积极分子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去过上10~12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们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政治学习以及“民主化”教育活动,使对战俘的管理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苏联管理人员非常善于利用日本战俘中存在的等级秩序,借日本军官来管理日本士兵,从而有效地完成劳动任务;另一方面,政工人员又推行“民主化”教育活动,试图消除日本战俘中存在的这种等级秩序。
当年的日本战俘山崎幸男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战俘自治原则,这导致了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克扣配给等情况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战俘营里也发生了反军方的斗争。”山崎幸男这里所说的“反军方的斗争”,就是日本士兵战俘反对日本军官战俘的斗争,而这种斗争自然是得到了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首肯的。
3、有日本战俘被发展为苏联情报人员
苏联还在日本战俘中发展了一批自己的情报人员,俄罗斯学者格列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2001年8月31日《独立军事观察》上发表的《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日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尝试着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否则,他们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国都会成问题。不过,并非所有的‘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的优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国……我们的特工人员在战俘们中间开展活动,培养‘自己的干部’。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产党员出现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俘营里充当苏联当局的秘密情报员,告发自己的同胞。”
每逢日本的广岛、长崎遭受美国人原子弹轰炸纪念日,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对日本战俘的态度相对于平时而言就会变得比较有人情味,他们会给战俘一些食品甚至伏特加白酒,安慰他们不要过于悲伤,同时也不忘记“责怪”几句美国人的无情,这时,动了真情的日本战俘有的会哭得很厉害,一些日本战俘还含着眼泪说他们憎恨美国人、热爱苏联人。
1949年初,日本战俘被准许与家人通信,每人先准许通一次信,用的是双页明信片,一页寄往家里,另一页是家人回信用的,回信地址是苏联XX地区XX号收容所,没有标明地名,明信片不允许写太多的字,苏联方面规定,战俘只准许写自己的事情,不允许介绍与自己无关的情况,在经过苏联方面的检查之后明信片才能由专人统一发出去,战俘民主委员会的委员可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多发几张明信片。
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报刊报道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年春天,正逢汛期,一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将不慎掉入水中的劳改营主任的儿子救了上来,此后,这名日本战俘在劳改营里的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观,后来当这名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的时候,劳改营主任眼含热泪送别了他。
岁月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当年救人的日本战俘,已经成了一个大老板,他打听到当年被他从水中救上来的那位小男孩的住址(这时,小男孩的爸爸——当年的劳改营主任早就去世了),邀请小男孩一家人去日本作客,还送给他们一辆崭新的豪华汽车。
不过,就笔者看来,当年这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与其说是苏联方面推行的政治学习、“民主化”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的成果,倒不如说是他渴求能够生存下去并平平安安地返回日本的求生本能和动机起了作用。
战俘问题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苏联劳改营对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现象,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问题跟一系列问题一样,长期以来一直被遮以神秘的面纱,以解密档案为依据,还历史以真实,无疑有利于世人对这段历史真实面目的真切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