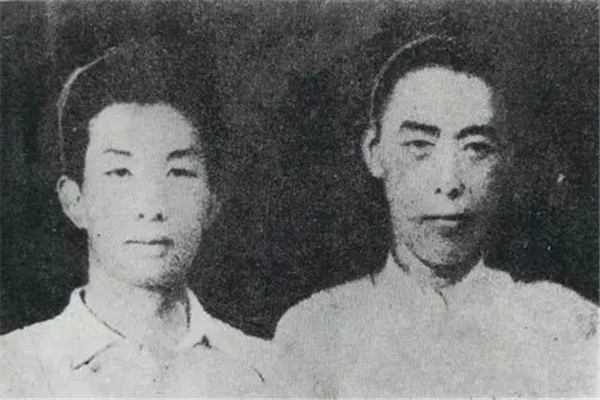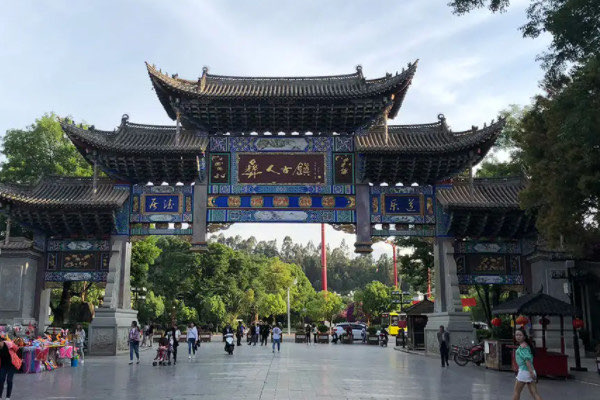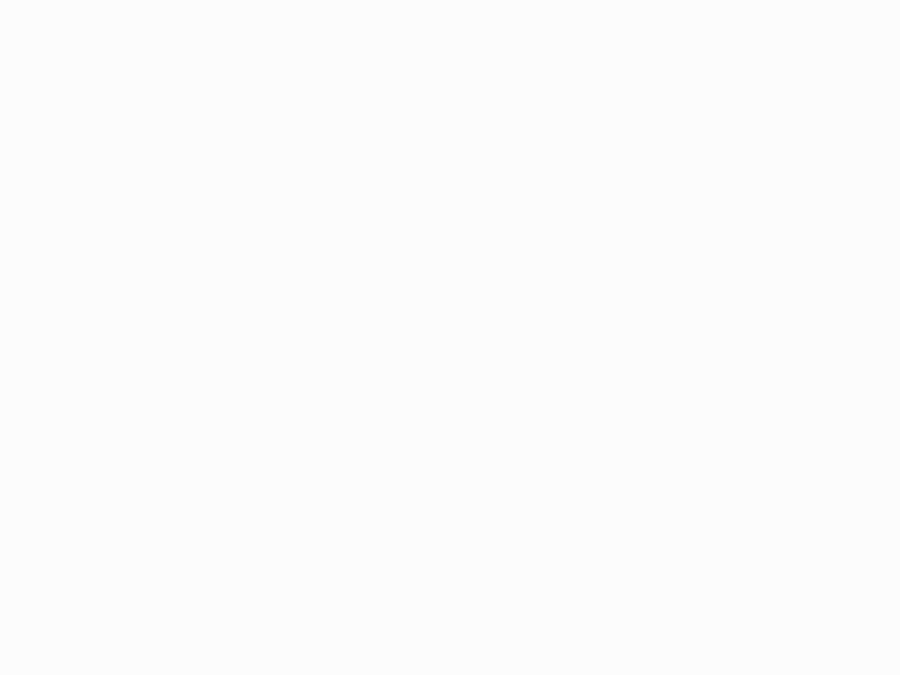近日,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把他对中国的思考结集为《我们的中国》,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在该书第一册《茫茫禹迹》的“自序”中,他这样说:“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这是本书的主题。”为此,李教授实地考察了很多历史遗迹,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趁李教授来上海参加新书发布活动之际,我们请他谈一谈如何认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澎湃新闻: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的讨论很多,“什么是中国”好像不再习以为常,对“中国”的认识似乎正在“去熟悉化”,您如何看待这些论述?
李零:昨天在复旦大学演讲,有人请饭,在座的朋友问,为什么我用《我们的中国》作这套书的书名。【趣探网】有位汉学家在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抢着说,说这个题目让他非常反感,好像我把他排除在外,是个分裂世界的人。其实,谁也没有禁止他从他的角度研究中国,也没有谁不让他加入“我们”。我跟他说,你可以从你的角度讲“我们”,我可以从我的角度讲“我们”,凭什么我就不能讲“我们的中国”。有些汉学家特别喜欢讲“不分彼此”,不分彼此是你跟他不分彼此,他跟你抬杠,且在那儿掰哧呢。我这套书,全书开头的题辞是闻一多的诗,诗中有一句“咱们的中国”。这话有人听了可能不舒服,说我是“民族主义者”。1840到1949年,中国血流成河,泪流成河,备尝屈辱,我不认为闻一多讲错了什么。现在,中国从任人宰割到独立统一,从被围、突围到入围,确实有很大变化,是不是因此我们就不能讲“我们的中国”了,一讲“我们的中国”就很丢脸,我不这么认为。
前几年,三联出过我的《我们的经典》。这套书是跟那套书配套。我写这两套书,主要是从正面讲中国。我用“我们”是为了表示我和与我同道者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见解,有别于当下流行思潮(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热)的看法。我的讨论跟汉学家没多大关系,跟周边国家怎么看中国没多大关系。要说有关系,也顶多是捎带脚,敲打了几下“解构永恒中国”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用中文写作,一点儿不脸红。不但不脸红,还把锻炼辞章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当作一种追求。我是用我熟悉的语言讲我熟悉的事,中文最合适。“去熟悉化”,这不是我的选择。我的预期读者是中国读者,我并不在乎汉学家的感受,谁听了高兴,谁听了不高兴。澎湃新闻:说到“民族主义者”,那该如何理解民族主义?李零: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个西方口头禅,右派讲,左派也讲,专门用来教训尚未归化或不听话的国家,咱们的同胞多半听不懂。
民族主义的民族是nation。这个词并不是中文常说的民族。中文常说的民族,现在叫ethnicgroup,nation是作为国家认同的民族。比如美国,它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只要入了美国籍,就是美国人。国籍(nationality)就是体现nation的概念。我们中国也一样呀,五十六个民族住在一起,都叫中国人。中国人的意思也是个国籍概念。欧洲所谓国,本来很小。申根国家是SchengenStates。一个state,也就我国一省之大,或者还不如。美国的国大,UnitedStates也是用state拼凑。他们说的现代国家是nation,nation的意思本来是族,跟在哪儿出生有关,跟native有关,state才是地缘概念的国。
欧洲喜欢讲自治。再大的国也是用小国拼凑。这个传统不仅对欧洲有影响,对它的殖民地有影响,就连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受它影响。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宁讲“民族自决权”,都有这个传统的影子。民族主义怎么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变成骂人话,这个帽子戏法怎么玩,说起来挺绕。欧洲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大约只有五百年,早先一盘散沙,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国家。他们的现代国家,主要出现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很多国家都是打出来的,反复打,反复重组,并非自觉自愿。上个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后有所谓“英国和平”,二战后有所谓“美国和平”,所谓国际秩序,全是打出来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想象的共同体”说,很有名。此说如指欧洲创建现代国家,试图把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不同的族群打乱重组,构建所谓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倒是挺合适,或指殖民时代,他们在亚非拉划分势力范围,对当地族群打乱重组,因而至今种族、宗教冲突不断的地区,也行。可是这顶帽子为什么一定要扣在别人头上,而不是自己头上呢?原因很简单。他们说,我们是过来人。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不再战,你们要想挑战国际秩序,自己玩一套,那绝对不行。因为这个过程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导致种族大屠杀,谁也别拦,我们一定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美国最爱讲爱国主义,爱国的国就是nation。他们有《爱国者法案》,就连导弹都叫爱国者。亨廷顿讲文明冲突,文明分三六九等。他们的国是好国,可以爱;你们的国是坏国,不许爱。关键在这里。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国际秩序也是打出来的。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西方汉学家试图“解构永恒中国”,解构的前提是建构,那中国是建构出来的吗?
李零:在这套书里,我想强调,中国是个历史过程,中国是个文明漩涡。它的前与后,既有连续,也有断裂,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他的内与外,既有辐辏,也有辐射,中心四裔,互为主客,也不是铁板一块。研究细化,可以,但不能闹到“白马非马”。中国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过程和地理概念,并非什么人所能虚构。近代中国也一样。“解构永恒中国”说的前提是,我们这个中国,不仅历史上是虚构,就连1911年后和1949年后的中国也是“想象的共同体”。你说的“建构”,其实是指虚构。澎湃新闻:现在史学界多提倡全球史和区域史,会把中国放到东亚里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方法是否会遮蔽了中国的特殊性,或者该问的是,中国是特殊的吗?
李零:中国当然是亚洲史的一部分,中国当然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我并不同意,我们的研究是汉学的一部分,我们跟汉学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当年,法国汉学开设汉、满、蒙三语讲座,王国维说,中国大学也应开设类似讲座。法国汉学研究中国,与西域探险有关。当时,蒙元史的研究、西北史地的研究在中国是显学。因为有五大发现,中法学者有共同兴趣和共同话题。美国的研究不一样。二战,美国血战太平洋,对东亚非常重视。战后的ChineseStudies主要是配合美国的战略研究。它是把中国、朝鲜和日本绑在一块儿研究。这是大的区域研究,小的区域研究,是把中国切开来研究。这是“解构永恒中国”说的真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