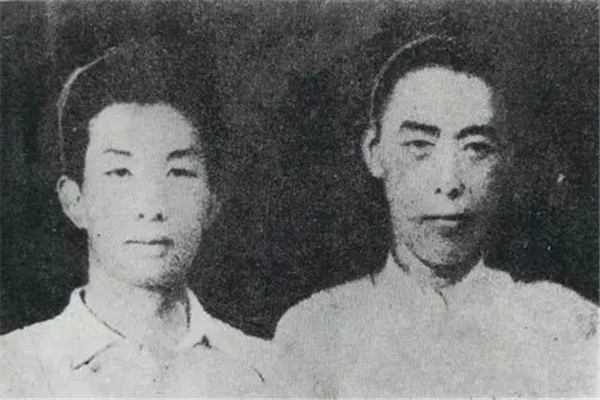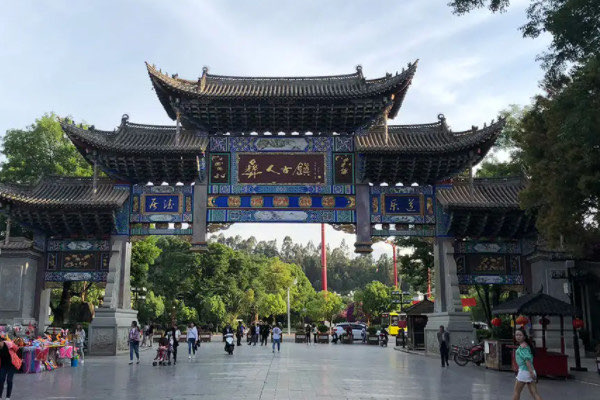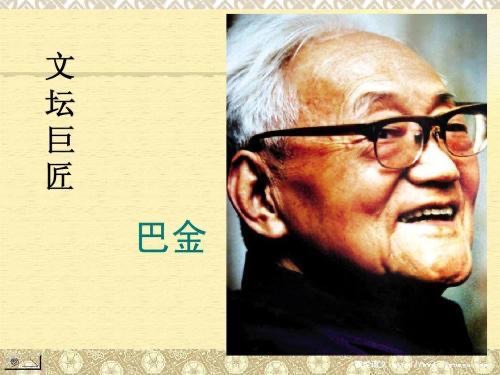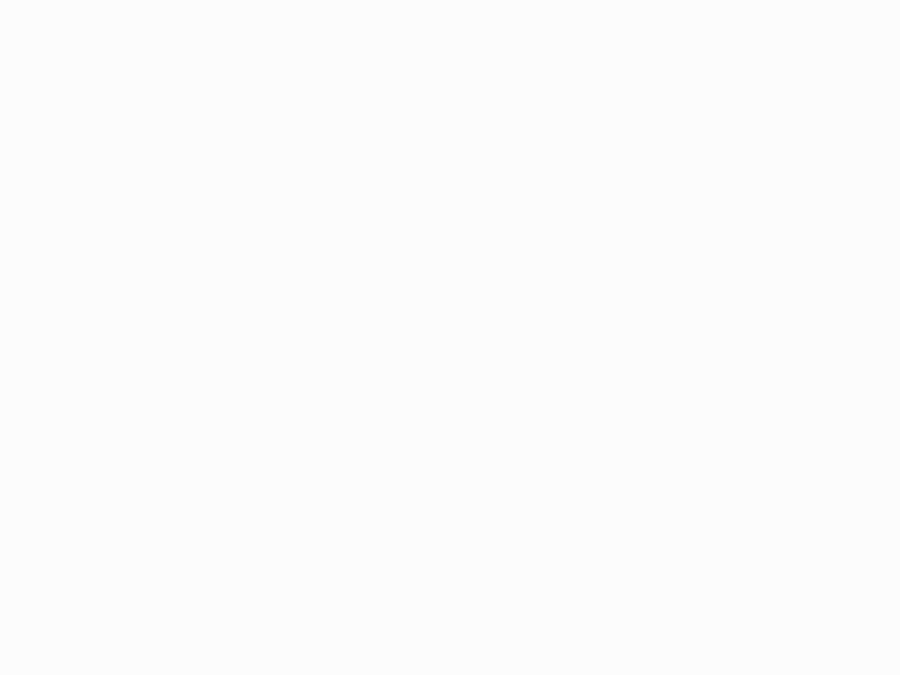一、《风》
二十几年前,我羡慕“列子御风而行”《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我极愿腋下生出双翼,像一只鸷鸟自由地在天空飞翔。
现在我有时仍做着飞翔的梦,没有翅膀,我用两手鼓风。然而睁开眼睛,我还是郁闷地躺在床上,两只手十分疲倦,仿佛被绳子缚住似的。于是,我发出一二声绝望的叹息。
做孩子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伴都喜欢在大风中游戏。风吹起我们的衣襟,风吹动我们的衣袖。【趣探网】我们张着双手,顺着风势奔跑,仿佛身子轻了许多,就像给风吹在空中一般。当时自己觉得是在飞了。因此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风。
后来进学校读书,我和一个哥哥早晚要走相当远的路。雨天遇着风,我们就用伞跟风斗争。风要拿走我们的伞,我们不放松;风要留住我们的脚步,我们却往前走。跟风斗争,是一件颇为吃力的事。但是我们从这个也得到了乐趣,而且不用说,我们的斗争是得到胜利的。
这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值得怀念的。
可惜我不曾见过飓风。去年坐海船,为避飓风,船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天气闷热,海面平静,连风的影子也没有。船上的旗纹丝不动,后来听说飓风改道走了。
在海上,有风的时候,波浪不停地起伏,高起来像一座山,而且开满了白花。落下去又像一张大嘴,要吞食眼前的一切。轮船就在这一起一伏之间慢慢地前进。船身摇晃,上层的桅杆、绳梯之类,私语似的吱吱喳喳响个不停。这情景我是经历过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轮船被风吹在海面飘浮,失却航路,船上一部分东西随着风沉入海底。我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今年我过了好些炎热的日子。有人说是奇热,有人说是闷热,总之是热。没有一点风声,没有一丝雨意。人发喘,狗吐舌头,连蝉声也像哑了似的,我窒息得快要闭气了。在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起一阵大风,或者下一阵大雨。
1941年7月9日在昆明
二、《雨》
窗外露台上正摊开一片阳光,我抬起头还可以看见屋瓦上的一段蔚蓝天。好些日子没有见到这样晴朗的天气了。早晨我站在露台上昂头接受最初的阳光,我觉得我的身子一下就变得十分轻快似的。我想起了那个意大利朋友的故事。
路易居·发布里在几年前病逝的时候,不过四十几岁。他是意大利的亡命者,也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不能和解的敌人。他想不到他没有看见自由的意大利,在那样轻的年纪,就永闭了眼睛。1927年春天在那个多雨的巴黎城里,某一个早上阳光照进了他的房间,他特别高兴地指着阳光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可喜的事。我了解他的心情,他是南欧的人,是从阳光常照的意大利来的。见到在巴黎的春天里少见的日光,他又想起故乡的蓝天了。他为着自由舍弃了蓝天;他为着自由贡献了一生的精力。可是自由和蓝天两样,他都没有能够再见。
我也像发布里那样地热爱阳光。但有时我也酷爱阴雨。
十几年来,不打伞在雨下走路,这样的事在我不知有过多少次。就是在1927年,当发布里抱怨巴黎缺少阳光的时候,我还时常冒着微雨,在黄昏、在夜晚走到国葬院前面卢骚的像脚下,向那个被称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个年轻异邦人的痛苦的胸怀。
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
水滴从头发间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雨点弄污了我的眼镜片。我的衣服渐渐地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模糊……白茫茫的一片……我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转弯时我也不注意我走进了什么街。我的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我的脚认识路。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马路,我不留心街上的人和物,但是我没有被车撞伤,也不曾跌倒在地上。我脸上的眼睛看不见现实世界的时候,我的脚上却睁开了一双更亮的眼睛。我常常走了一个钟点,又走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我回到家里,样子很狼狈。可是心里却爽快多了。仿佛心上积满的尘垢都给一阵大雨洗干净了似的。
我知道俄国人有过“借酒淹愁”的习惯。我们的前辈也常说“借酒浇愁”。如今我却在“借雨洗愁”了。
我爱雨不是没有原因的。
1941年7月20日
三、《雷》
灰暗的天空里忽然亮起一道“火闪”火闪(四川话):即闪电。,接着就是那好像要打碎万物似的一声霹雳,于是一切又落在宁静的状态中,等待着第二道闪电来划破长空,第二声响雷来打破郁闷。闪电一股亮似一股,雷声一次高过一次。
在夏天的傍晚,我常见到这样的景象。
小时候我怕听雷声;过了十岁我不再因响雷而颤栗;现在我爱听那一声好像要把人全身骨骼都要震脱节似的晴空霹雳。
算起来,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还是个四五岁的孩子,跟着父母住在广元县的衙门里。一天晚上,在三堂后面房里一张宽大的床上,我忽然被一声巨响惊醒了。房里没有别人,我睡眼中只见窗外一片火光,仿佛房屋就要倒塌下来似的。我恐怖地大声哭起来,直到女佣杨嫂进屋来安慰我,让我闭上眼睛,再进到梦里去。在这以后只要雷声一响,我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会马上崩塌,好像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了。不过那时我的世界就只是一个衙门。
这是我害怕雷声的开始。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更后,雷声又给我带来一种新的感觉。每次听见那一声巨响,我便感到无比的畅快,仿佛潜伏在我全身的郁闷都给这一个霹雳震得无踪无影似的。等到它的余音消散,我抖抖身子,觉得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巨声,我多半已经埋葬在窒息的空气中了。
去年,一个昆明的夏夜里,我睡在某友人的宿舍中,两张床对面安放。房间很小,开着一扇窗。我们喝了一点杂果酒,睡下来,觉得屋内闷热,空气停滞,只有蚊虫的嗡嗡声不断地在耳边吵闹。不知过了若干时候,我才昏沉沉地进入梦中。这睡眠是极不安适的,仿佛有一只大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胸上。我想挣扎,却又无力动弹。忽然一声霹雳(我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响雷!)把我从梦中抓起来。的确我在床上跳了一下。我看见一股火光,我还没有睡醒,我当时有点惊恐,还以为一颗炸弹在屋顶爆炸了。那朋友也醒起来,他在唤我。我又听见荷拉荷拉的雨声。“好大的一个雷!”朋友惊叹地说。我应了一句,我觉得空气变得十分清凉,心里也非常爽快,我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今年在重庆听见一次春雷,是大炮一类的轰隆轰隆声。“春雷一声,蛰虫咸动。”我想起那些冬眠的小生命听见这声音便从长梦中醒起来,又开始一年的活动,觉得很高兴。我甚至想像着:它们中间有的怎样睁开小眼睛,转头四顾,怎样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然后一跳,就跳到地面上来。于是一下子地面上便布满了生命,就像小说《镜花缘》中的故事:因为女皇武则天的诏令,只有一夜的功夫,在隆冬里宫中百花齐放,锦绣似的装饰了整个园子。这的确是很有趣的。
1941年7月16日
四、《月》
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么?
圆月有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罢,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中,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冬季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为什么还有篰娥奔月的传说呢?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么?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罢。
1941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