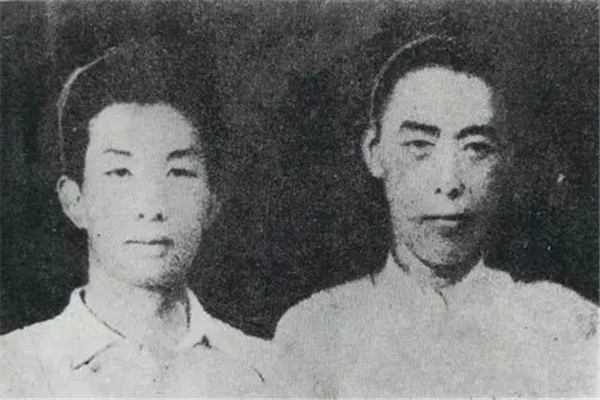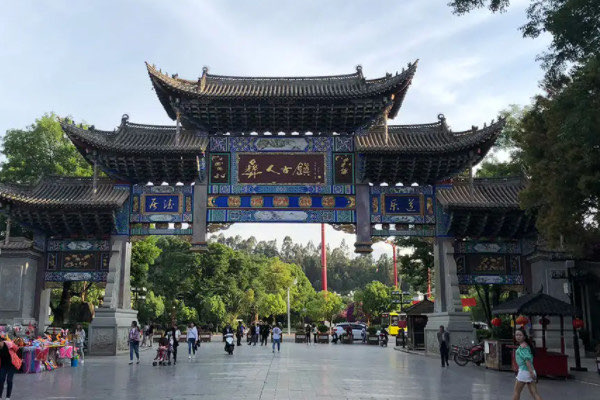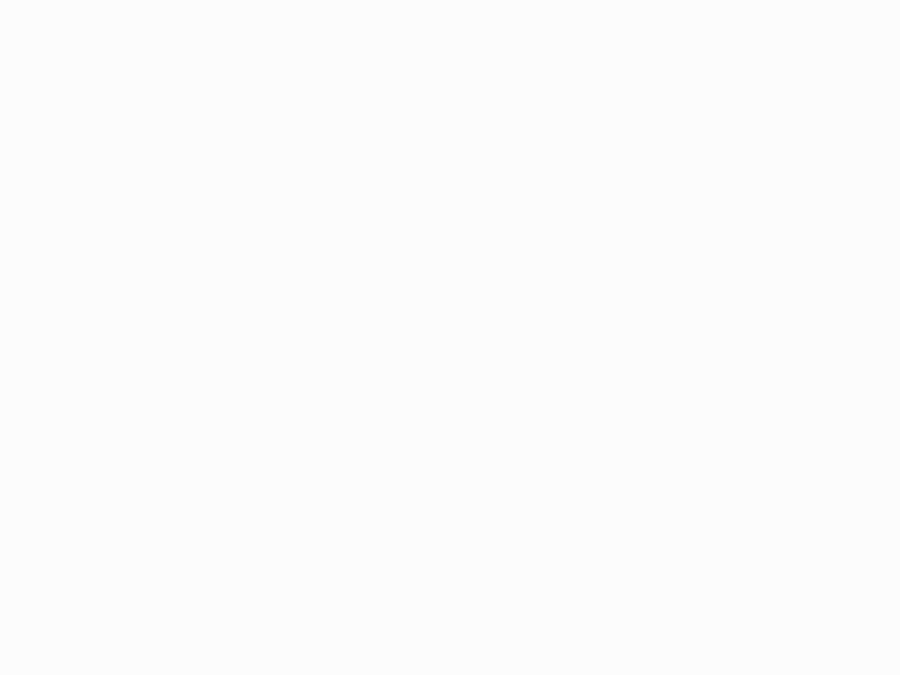散文一:《笑》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趣探网】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散文二:《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子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难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追忆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性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
散文三:《母爱》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院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里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小船般散漂在水里。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倚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地倾斜过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也不摇动了。雨声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不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地受了感动——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盖天空下的隐蔽?
散文四:《小桔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反反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1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母亲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 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暗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母亲。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的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母亲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1个大髻。门边1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母亲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1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1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父亲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母亲的枕头边。
小桔灯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更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1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洋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父亲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母亲就会好了,一定!”她用小手在面前画1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泪水在我眼中打转……
散文五:《再到青龙桥去》
前几天,我又到青龙桥去,访问了那边的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的青龙桥分队,上了长城……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
再到青龙桥去的动机是这样的:三十七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曾经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到青龙桥去,回来写了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好久以前,就有朋友建议,说我应该再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国庆日,我决不肯离开这腾光溢彩的北京城!我抽了个空,和两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庆之前,去偿了这个夙愿。
再到青龙桥,决不是“寻梦”,因为从恶梦中挣扎醒来的人,决不要去“寻”那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梦;同时也不是“访旧”,因为你去访的对象,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是更年轻的而不是更老迈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还是打一个新比喻好一些:比方说你是去访问一个久病新愈的朋友,他是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的;你是去看一丛新栽的小树,它们是年年地更加高大更加浓密的。你不准备去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地自寻烦恼,你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而且时时给我挑起崭新的喜悦:张灯结彩的西直门车站;花卉缤纷的车站广场;车站上梳着双辫的收票的大姑娘;和车上手里拿着蝇拍笑嘻嘻地来往招呼的车务员小姑娘;车窗外掠过的一幢一幢新的工厂和学校的建筑,以及连成一大片的青葱的田野;而最耀眼的,还是田野边站着的带着红领巾的儿童;万绿丛中,鲜红一点,内中含着多么新鲜的诗意呵! 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衣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铡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反动派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反动派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 “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