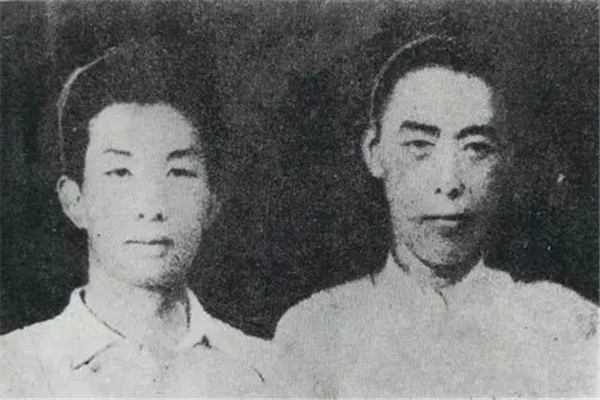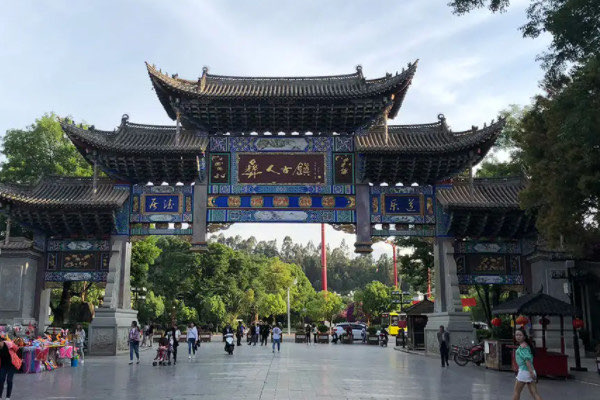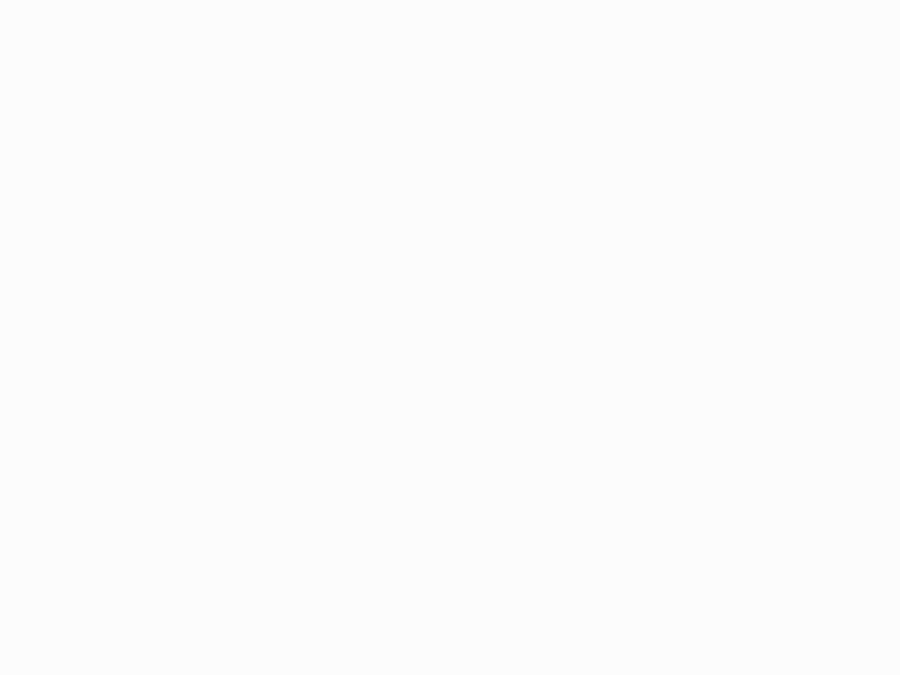1、《姻缘》
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做“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趣探网】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
“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
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
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怵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惟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
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
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
“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
“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
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
一九九二年春节
2、《第一次盼望》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盼望。那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
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怎么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就去吗?嗯。
这段时光不好捱。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那上面有一群比我大的女孩子,一个个都非常漂亮。我蹲在草丛里看她们,想像她们的家,想像她们此刻在干什么,想像她们的兄弟姐妹和她们的父母,想像她们的声音。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
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呢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我不是一直在等着,母亲不是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一件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
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再去。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决不许她再耽搁。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儿明白了。
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遽的变化,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卡嚓卡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男孩儿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男孩儿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3、《故乡的胡同》
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
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
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陶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
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
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
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
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诌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
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
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
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
一九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