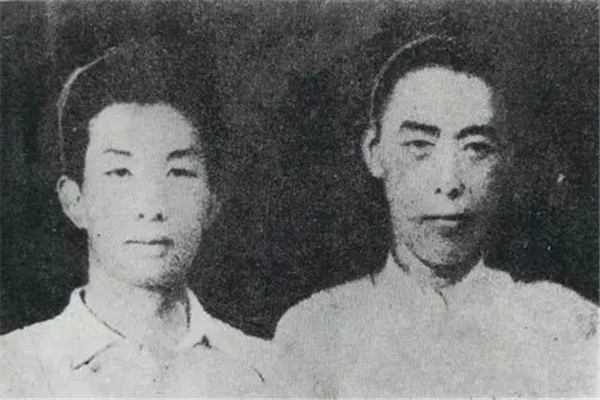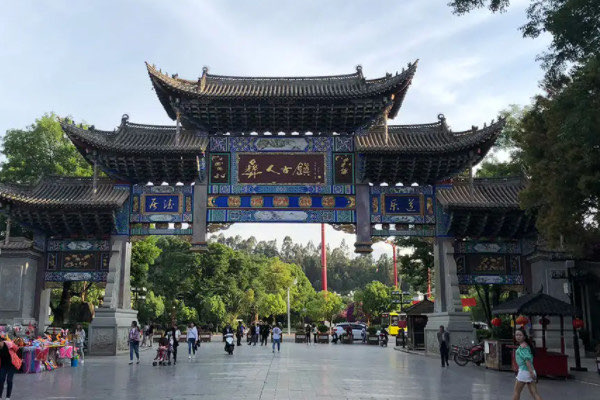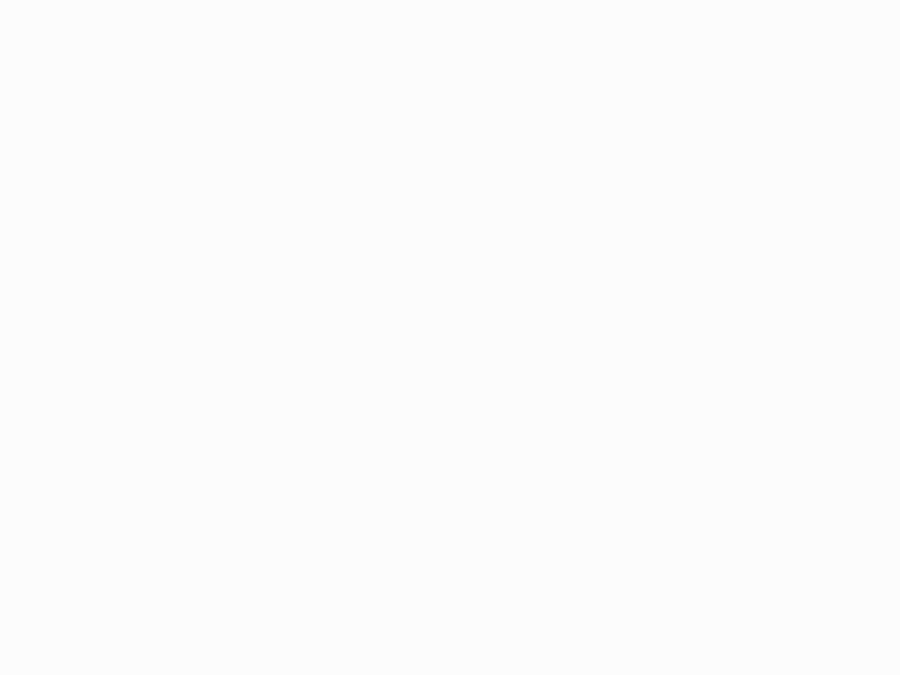描写手艺人的散文篇一
小时候的农村,各种手艺人层出不穷。那时有句俗话叫“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所以有一技之长的兼职农民家庭往往比纯粹的农民家庭要富裕一些。在我还小的时候,乡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手艺人,补锅的,打铁的,剃头的,木匠,石匠,裁缝,反正各种各样的手艺人,组合成农村芸芸众生。时间的河流湮没了儿时的记忆,一些传统的行业正在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可能只是瞬间,而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却被定格为永恒。
时间回放到三十多年前,乡村的胡同、城市的街巷里经常可以看到锵剪子磨菜刀的,扒盆补漏锅的,挑着担子理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同里的叫卖声连同“响器”发出的各种声响逐渐消失了,很多老行当也随之逐渐消失,透过这些消失的传统手工艺人,可以感受到乡村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趣探网】
过去,人们常能在乡间见到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他们肩扛长板凳,板凳的一头放着磨刀石或手摇砂轮,另一头搭着个麻布袋,袋里装有锤子,锵子等工具,凳子腿上拴着个小水桶。那“磨剪子来锵菜刀”婉转的吆喝声回荡在小胡同中。家中爷爷奶奶听到这种声音便知道磨菜刀的人来了,拿出家中不好用的剪子菜刀交给磨刀师傅打磨。
记忆中,常来我们村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磨刀老头儿,一双沧桑的老手至今我还有印象。老头儿为人憨厚谦和,干活细致手艺好,每当他走进我们的村庄吆喝几声,很多人家的刀剪都愿意拿出来请他打磨。
记得有一首歌里唱到:“国家变化这样多,你家的剪子菜刀还得磨。”离开家乡来到城里定居,偶尔在饭店的门口还能见到锵剪子磨菜刀人的身影,但他们的操作工具都换成现代化的了。
过去在乡村经常见到的除了锵剪子磨菜刀的,还有扒盆补漏锅的,农村使用的一些小型生产用具他们也会修理。扒盆补漏锅的走街串巷,吆喝的“扒盆——补漏锅”嘹亮的嗓音绕梁不绝,婆娘媳妇们忙找出自己的破锅烂碗拿到扒盆补漏锅匠前让其修理。其实,在乡间,扒盆补漏锅的按修理东西的品种来决定工程的不同。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例如,有修土盆的’,有专门补锅的,补搪瓷器皿的,补铝锅水壶的,技术、火候各不相同。当然,有一些大师傅可以“通吃”,他们的技术水平比较高,对各种活都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扒盆补漏锅的所用的工具比较简单,最早的一般都担一个挑子,挑子里放着各种工具和零部件,后来逐渐换成用自行车驮着两箱行当行走在乡间陌里。印象中,扒盆补漏锅的来到乡村中的大树下,刚停下车子,就有人拿出自家的物什到他这里修理。只见他拿起锅碗瓢盆,叮叮当当一阵响声之后,盆上的裂纹用“扒拘子”扒上了。换锅底时,不时传来敲击铝板发出的“呱哒呱哒”声打破了乡村的寂静,当渗漏的锅底换成了新的时,有意思的是,扒盆修理锅的还不让主家拿走,装一锅水,试一试漏不漏,还信心十足地说:“漏了,我一个钱都不要!”现在,一些头脑灵活的扒盆修理锅的匠人,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开始琢磨修理高压锅、电炒锅、电饭煲了。时代在迫使每一个人前进,手艺人又怎么能够例外呢?回想起来,我们真的应该感激当年那些手艺人,是他们一年四季栉风沐雨,用手艺帮扶着父老乡亲渡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活中的“难坎儿”。如今,这些手艺人大多已经去世,即使尚在人世,也入耄耋垂暮之境。想起当年他们的娴熟技艺和奔波忙碌的身影,一种怆惋之感袭上心头……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蓦然发现,当年乡村的许多手艺人,而今早已不见踪迹。岁月沧桑,变幻着一轮又一轮的宿命,无论是城市或者农村里的人,端着烫热的二两小酒,掰着炒熟的花生,品尝着美酒和花生米的余香,那些乡村曾经的手艺人,最终成了人们的一种怀想。
描写手艺人的散文篇二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手艺与文化正走的无声无息,“手艺人”这一称呼也离我们愈来愈远。
曾经也问过妹妹,我问她是否知道爆米花时这么做的,她居然告诉我是用豆子敲裂了炸的,真是让我哭笑不得。我费尽口舌的向她展示我童年看到的爆米花的做法,而她却无法理解。
或许是深秋,或许已入冬,我在阳台上写作业。已是旁晚时分了,忽听得“嘭”的一声,抬头,顺声而望,只见夕阳已落,晚霞已红,在楼下一棵正落叶的树边是一位爆爆米花的老人。现如今想想,那是何等的意境!便丢下笔,兴冲冲的去找妈妈,妈妈便找来了个袋子,装上几把大米,我在一旁却嫌不够。人们三五成群的围在老人的小摊子边上,每一次响声过后,那还算恬静的树下便有了各种声响:小孩子的欢笑声,塑料袋的声音,妇女付钱砍价的声音。一会儿又静下来,那样的乐此不疲,繁中生乐。
好不容易轮到我了,我在一旁小心地看着,在我看来,把硬邦邦磕牙的米粒变成又香又脆的爆米花实在是件奇事!那老人把米倒进炉子里,又从旁边黑乎乎的盒子中挖了勺白糖,我多希望他能多放点,他便一次又一次的摇动手柄,炉下的煤炭烧得通红,我喜欢站的近些,那老人便会和我说话,有的没的我们聊着。一会儿,他便会高声一呼:“要爆喽——”我便捂着耳朵跑向妈妈,“嘭——”如一声闷雷,在我看来,这比一样烟花还要精彩。
米粒与白糖的结合成了我童年的滋味,空气也变得如此香甜,我喜欢用手把爆米花刨出来,满满两大袋,如同堆沙子般有趣。付完钱,妈妈一手拎一袋,袋口冒着热气,我总伸手去抓一把,先是一粒一粒的吃,一把一把的吃,最后将整个嘴巴塞了个满,满足与喜悦充溢着整个口腔。若换成什么稀罕物,像是巧克力,一次只有那样的一小块,哪能带来如此的满足感。
回家后,解了袋子,索性将整个脸埋进爆米花里,乱嚼几口,还带着些温热,鼻间香气正浓,妈妈见了便呵斥一声:“干什么呢!”我一抬头,嘴上,鼻尖上,睫毛上如点点白雪,妈妈便会笑个不停。
现在回忆起这些童年乐事,手中执笔依旧,楼下越是另一番风景,怎叫人不心生伤痛。